
他被誉为中国“身价最高”的记者,二十载孤军深入从事揭黑调查报道,曾有恐吓者扬言,用五百万招买他的项上人头。
他又被认为是最清贫的记者,连续八个月无任何收入,只盼用笔尖冒死为民请命,曾有数篇重大新闻报道,获国务院两任总理直接批示。
将心比心,把人当人,投身公益,信仰人道,他倾尽全力挽救六百万身处遗忘边缘的尘肺病人,在他看来一切只是换了个战场。
大爱清尘公益项目,从艰难起步到渐获认可,面对眼前痛苦与绝望,他依然呼喊那句悲壮的口号,能帮一点是一点,能救一个是一个。

【采访实录】
当你对一个人或一件事爱莫能助时,那种拒绝对自己是很沉的心理负担,为何还要强求这种敏锐的痛感?
王克勤:我现在到今天为止还有大量的追求公平正义的苦主们,到现在还给我打电话,因为我已经不在媒体行业,已经从媒体下岗了,当我无能为力的时候,我觉得至少有一点是可以救的,倾听并安慰,为什么,我自己曾经做过上访者,在2001年的时候,我当年在甘肃因为做一系列的报道,而后被一个莫名的理由开除公职,我就觉得我冤透了,我上访,好多人说为什么不走合法的程序,合法的很多程序是走不通的,就像很多人有大量的访民,按道理来讲,在司法独立的国家,遇到任何问题我们去找法律,用法律去裁办,问题我们不是一个司法独立的国家,所以只能仰仗于最高行政权的力量来解决问题。
作为一个新闻人和公益人,在角色上有什么相同和有什么不同?
王克勤:过去20年做调查记者,是为了遏制伤害,遏制犯罪。今天做公益是为了基于人道的考量,捍卫每一个生命。因此,新闻生涯和这两三年来做的公益事业,自始至终都在做着同一件事情:捍卫每一个生命的尊严和权利。只是换了个战场而已。
作为调查记者,20余年您追逐真相,但似乎真相这个词在当下被媒体滥用了。当一个人在自我标榜真相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否定了其它事实的真实性,甚至容易做为在观点上排除异己的正当理由,您如何评价?
王克勤:记者追求真相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不是为了追求真相而追求真相,不要把手段当成目标,手段永远是手段,刀永远是工具,要为目标服务,要为你的理念服务。大家经常会讨论一个问题,有一人掉进水里,王老师你是去救人,还是去拍照?我说我去救人,他说你不是记者吗?我说对不起,我娘生我的时候我才是人,这是一个常识,然后我的人生选择了一个谋生的职业、行当,这个行当叫记者。
第二我是一个公民,公民不仅拥有公民的权力,公民也当履行公民的责任与义务,公民责任你就要有明确的概念,当看到另一个公民受到伤害的时候,你也有责任和义务施以援手,这是公民的责任和义务。而公民责任和义务亦然建立在人道的基础上,人道是人类的基础常识。你不能看着另一个生命被涂炭或者一个人掉进水缸里,你举手之劳就可以救他人水火之中。
20年新闻生涯不断接触社会阴暗面,看到底层疾苦,容易产生压抑和焦虑,有过这样的内心挣扎吗?凭借什么依然相信希望和美好?
王克勤:在痛苦中发现希望,这是我这些年很深的体验。
怎么解释?
王克勤:我跟你说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就像中国这些年面对的一系列的拆迁问题、征地一系列的冲突,发生过一系列悲惨的故事。这几个悲惨的故事当呈现在你眼前的时候,说明遭遇这些故事的人已经开始觉醒或部分觉醒,他们不再做沉默的羔羊,他们开始要呐喊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寻找记者,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来争取可能的权利,这个本身就是一种觉醒。
好多人说你们是大公无私的一批人,我说这话错了,我们不是雷锋,我们就是志愿者,普普通通的志愿者,我们做这些事情牙根就不是大公无私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我们为了自己的内心才持续前行。
无论是做记者,还是做公益,无论之前还是现在,甘于清贫都是您的标签,以您的资历和影响力,完全能在市场化媒体或企业公益中寻得归宿,并获得物质补充,为什么不为所动,是有意保持距离吗?
王克勤:我并没有刻意要保持清贫这样一个姿态,说个实在话,人类的需求是一个分层次递进的需求,我也想有好的吃穿住行的生活保障,给自己家人,给自己的父母,给自己的孩子,这是一个基本的、正常的心理。但是很多人很多的具体情况因人而定,更重要的是每一个要有自己的处境,更重要的是在关键的原则性问题上要有自己的坚守。2001年底2011年差不多是10年的时间。而这个10年是我被业界称之为最清贫的10年,我觉得好多人都在问,说是《中国经济日报》,你当时10年时间一直拿着很低的工资。
我刚到《中国经济时报》基本工资是1000块钱,2002年。我离开《中国经济时报》基本公司是1700。也就是我离开《中国经济时报》是2011年的年底。印象最深是2007年冬天大概11月份,有一天早上我起来一摸腰兜里总共大概是8块钱,当天晚上有人就送来10万人民币。
用什么来抵抗这样的诱惑,坚持的是什么?
王克勤:我在做监督的过程中,我得罪了很多的人,你明白吗?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被你监督或者被送进监狱的任何的一个人,可能都会伺机致你于死地,你不能给别人创造这个机会,作为监督的人,尤其长期作为监督的人,你必须给自己在道德层面有圣女一样的要求,你才有战斗力,才能会立于不败之地。但是我觉得人怎么看待人生的,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好多人也很失败,我的一些同学,尤其是我当年初中和高中的一些同学,他们就用一种非常世俗的概念来看待人生。
我儿子认为我很成功,我父亲认为我很成功,虽然我给他们创造财富,自己还局促在北京,我儿子曾经对我的点评是我爸爸比一个省委书记要成功的多,我觉得就足以了,我说我对不住你啊。人生的收获是两个层面收获,一个是物质层面收获,另一个是精神层面的收获,精神层面和灵魂这样的一个快乐感觉的收获,拿钱买不来才是最具珍贵的。
我觉得我父亲对我的人生影响非常大,他是乡村教师。严格的讲这种“士”的精神在他身上,应该是比较经典的。所以他把这些东西又不断地灌输给我,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我父亲就跟我讲,他说工作上要向好的看齐,生活上要向差的看齐,这不仅仅是我上小学的时候,我父亲跟我讲的,这些年老爷子还跟我这样讲。
我老婆有一句话我觉得还是蛮经典的,我曾经在2004年的时候,本来要在北京的土桥那边买房子,那时候房子挺便宜的。然后后来好多朋友来帮我,等于大家借款给我买房子,我当时就表态我说赶紧买房子。然后我老婆回家以后坚决不同意,我说为啥?我们借了钱,然后再还账不就行了吗?
她说,当你背上债之后,眼睛睁开,钱是出现你在眼前的一个字,因此只要出现各种情况的时候,你将会把钱作为你日常生活考量的第一要素,你就没有办法保证你的特立独行,就没有办法能够坚守你的原则。
严格的讲2001年我在甘肃的时候,在新闻专业主义,新闻的整个坚守这一块并不是今天这样做的,当时参加什么新闻发布会,去拿车马费对我来讲很开心。
您也拿过车马费?
王克勤:拿过,我公开承认,拿土特产品,拿过,这是在2001年我在甘肃地方做记者时这样子,人都要真诚的坦诚的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这样一个立场。
13年前的现在,为了写兰州证券诈骗案,受到死亡威胁,把妻儿送到远方,只身面对。为公还是顾私的选择一定经历了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痛苦。
王克勤: 2001年是我叫做人生炼狱的一个阶段,2001年那会是把兰州股票黑市案报道做出来,在做报道的前期实际上这个事情就已经,因为我采访的,我历来采访的作派是很扎实的,海量采访接触的人很多,大家都知道,并且已经接到过很多恐吓电话。
什么样的电话,怎么说?
王克勤:要血洗我的家庭,传呼机发信息来说要血洗我的家庭,打电话到我办公室要恐吓,要杀掉我。因为我采访的是十多家非法的企业,有黑社会性质。我要断他们的财路,他们就要断我生路。最后我觉得我要把老婆孩子送走,是我自己选择了这个,不能让老婆孩子全祸害进去,所以就把老婆孩子打发走,女人和孩子离开战场。最糟糕的时候四位警察荷枪实弹的住到我家里陪着我。我也不知道哪一个人要搞死我,走到街上就有点惶恐,害怕咱们也是命,咱也是个人,那个是期间一个警察,一个很好的朋友给我送了一个武器,我大概这个武器配了将近一年时间。
说实在的是我也害怕死,咱们也是个命。但是晚上眼睛一闭上,就想到被整惨和被整死的一些人,他的家属在我面前跪倒流泪,在向我求助。我就觉得总得有人站出来给他们说话,总得有人第一个去堵枪眼。
社会上有传言,王克勤过多顾虑别人的家庭,别人的感受,那么对于自己的妻子孩子考虑的并不那么多。您喜欢喝酒,喜欢喝酒的媒体人一般都是性情中人,往往在这方面的决断上是非常痛苦纠葛的。
王克勤:我觉得我今天走的这一步和走的今天这种程度,最大的支持者当然是我老婆,我犹豫过,我曾经试图放弃,我曾经想去经营系统,或者其他挣钱的媒体去做事。但我老婆认为好的地方不一定适合你的地方,在适合你的地方做适合你的事情,男人一辈子总得有所作为,做一番给天地交代的事情,然后面对诸如像恐吓的和这种风险,但为什么走到现在,有非常重要的概念,信仰。他们家祖祖辈辈是虔诚的佛教徒,他认为我做的这些事情是救众生于苦难之中的事情,从当年揭发黑幕到今天大爱清尘,认为是在行菩萨道普度众生之苦难。
2013年12月,国务院印发《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扩大社保覆盖面。加大对尘肺等矿工职业病的预防和救治。这个规划对于尘肺病人和关注尘肺病群体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王克勤:我们至少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转折,2011年尘肺病问题曾经因为会引发一些维权和社会冲突,所以曾经是一个比较敏感的维稳问题,在2010 年、2011年的时候很多地方政府对尘肺病大概就是打压和控管的,尘肺病问题不禁得不到重视,反过来是搁置的,或被隔离,那么到2012到2013年底, 国务院正式有一个国务院的官方文件里,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提法,要加强对尘肺病的这样一个防治与预防与救治的力度,也本身是一个态度,有了态度才可能有行 动,那么态度是基础。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规划出台后,并没有一个很详细的一些意见,对下一步的政策推动有什么期待?
王克勤:整整做了将近4个念头,近3年的时间,到现在累积我们总人口也不到一千人,筹集的资金也不到1200万,救的人只有不到一千人,相当于像我们这类 申请要求救援的农民总人数的千分之一,相当于中国尘肺病农民总人数的万分之一,因此,我们有着深深的无奈感无力感,感觉靠这样一个民间组织点点滴滴的救援 不了六百万甚至上千万尘肺病农民的救援。
我们算了一笔账,一个尘肺病农民抵一万元的救济经费,至少就需要六百个亿,一个人如果给12人民币的救助和保障资金,就需要六千个亿,这不是任何一个公益组织所能够承担的。我们认为大爱清尘最终是要推动国家行动,让国家整体接盘。更重要的是让国家通过立法的手段来遏制尘肺病在中国的再生,因为尘肺病说的直接一点是人祸,慢性的。
这么多次探访当中,印象最深的一个尘肺病人生活状况如何?
王克勤:对我印象最深的,迄今为止我认为还是2012年的8月19号,我在陕西旬阳县有一个叫红军乡,见到的一户尘肺病家庭,在一个大山的半山腰见到一个农户,这个农户是36岁的尘肺病农民石发学,见到他的时候,他是尘肺病三期的一个重症尘肺病患者。
当时在他家的小院里我看到一个老人爬在地上,面前放着一个黑色的盆子,黑色的盆子里放着一些黑色的东西,这老人在吃这些黑色的东西,当时我的感受就觉得那就 像一头猪,一条狗。后来我知道这老人是石发学的叔叔。2013年的1月23号,一个坏消息传来,石发学撒手而去。与此同时我们听到一个,我当时听到一个更 让我痛心的消息,由于石发学长期的尘肺病,失去劳动能力,家里没有任何经济收入,妻子无力安葬自己的丈夫,在村里挨门逐户求亲求友,佘了一口棺材让厍发学 得以入殓。我听到这个信息以后,我觉得心是撕裂的一种疼痛,因为这样一个农民,这样一个中国人如此低微低贱死亡的时候,连棺材都没有死亡的时候,正是这个 国家应该自省的事情。
在湖南探访中你提到,其中一对尘肺兄弟有可能还伴有肺结核,你很担心,为什么?
王克勤:因为在尘肺病患者群体里,并发肺结核的人不在少数,一方面我在担心患者,因为尘肺病人得了尘肺病,同时并发肺结核,会给他的家人带来生命的威胁,肺 结核是传染病,同时我有一种深深的忧虑,我们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一直在为尘肺病人奔走,都在跟尘肺病人进行着近距离的接触,我们的志愿者也是一个一个鲜活的 生命健康的生命,我不希望我们的志愿者在救援农民兄弟的过程中,被肺结核所伤害。
历次探访与对尘肺病人细致的核查,必然需要一定的成本,目前为止运营资金困难吗?
王克勤:我们的行政成本对大爱清尘来讲,是大爱清尘目前最大的难题,说白了,大爱清尘到现在能救这么多人,发生的行政成本非常的小,对大部分公益机构和绝 大多数的人是不能理解的,我们大量的志愿者在一线去探访,就像我刚才说的做这些工作是自带干粮,自掏腰包,前往救援,从2013年开始我们才开始对部分地 区一线探访的工作人员的交通费和住宿费进行报销,而此前是没有的,为什么没有,说白了最根本的问题是大爱清尘首先筹款难度系数非常大。
难在哪呢?
王克勤:从公众层面来讲,人类有一个天性,趋利避害,所有的人正常的人,都喜欢可爱的孩子和美丽的女性,没有人非常喜欢死难,而大爱清尘正好是与孩子、女人与所谓美好的这些视觉印象无关的,是大量的生死之间救命的项目,甚至常常面对死难,所以公众对这个项目敬而远之,大家从心底里都觉得这是救命非常重要, 但大家都不愿意参与。我们的整个募捐人员到企业里去,打开我们的视频资料一看,有死难的,企业的老板就说你走,你别给我放这个东西,这是我们的募捐的整个 人员在外面的遭遇。但对我来说,我是人,我的血里流着人血,看到人在那里放命,生死之间,我觉得我在生死之间,我想干,我不干我坐不住我受不了。
2011年6月15号起步到6月28号整整过去13天,大爱清尘面向全国的公益项目的公共帐号只有三笔捐款,2500块钱,其中一笔还是我们自己捐进去的,最初跟着我干的几个年轻,说王老师搞不下去了,没戏唱了。感谢互联网,感谢微博。于是从6月15号开始我就持续的发微博,不断的发微博,疯狂的发微博,6月28 号,23点03分,当时的微博女王姚晨转发我的微博,接着7月份就有很多的大V转,一个月捐款40万,有钱才能救命,有钱才能救援,这样大爱清尘在8月1 号第一批患者送进医院,大爱清尘的救援就开始滚动起来。到2012年、2013年中央财政开始支持,中央财政给我哪怕一块钱我都感恩戴德。
20年前,初出茅庐的王克勤,对职业生涯有什么期待?
20年前我刚起步的时候没今天这样的系统想法。我刚毕业的时候很功利,就想当官。我1984年毕业,我是中专毕业,当时中专是很厉害的,组织部选拔的后批干部,年轻人眼里简直是一个让很多人眼睛发绿的岗位,但是我天生不是做官的材料。讲一个例子,市里的主要领导到我们部里来开会,周四下午的政治学习,我傻到什么程度?我当时太19岁、20岁,中午会议中间休息的时候我就跟过去跟市委书记聊天,没高没低的小年轻,20岁啥也不知道就聊。我觉得领导也就跟我们平起平坐。回头组织处的处长,找我谈话,说我无组织无纪律,目无尊长。我当时不知道哪地方出错,我认为没错。我不适合在官场上混,官场上八面玲珑,四面逢源,咱不行。
我记得当年我一个同学,这个兜着一包烟高级的,那个兜里装着烟低级点,见着我同学把低级的烟掏出来,一不小心把这个烟拿出来,高级的烟拿出来以后赶紧又装进去,把差的烟拿出来,我就发现人家是投机的人。
2001年春节,打电话给远方避难的妻子,其实有一点临别感言的意思,有因此掉过眼泪吗?
王克勤:你说呢?这是正常的。
那你依然选择这条路。
王克勤:鬼子进村面对罪恶,面对魔鬼,总得有人站出来,第一个拿起大刀干,如果人人坐在那里无动于衷,那么整体的坐以待毙,虽然站出来第一个拿起大刀站干的人可能会死得很惨,但未必每一个人都会死,当你站出来的时候就可能会赢得机会,就可能会赢得改变。
凤凰公益:在王克勤看来目前的中国最大的公益是什么?
王克勤:我个人以为最大的公益,依然是救命。
【记者后记】
第一次来到大爱清尘的办公地,难掩震撼。因为在中国,有600万尘肺病人企盼着,在这样一间不大的两居室里,能衍生出他们与他们家庭生存下去,找到尊严的希望。似乎与王克勤扯上关系的地方都不难找到清贫的标签,局促的办公室堆满了简陋的物料与办公用品,甚至让摄像机与灯光都难以容身。采访在拮据的气氛下进行,虽难言电视效果,却也记录实态。屋内唯一无法遗漏的饰品是挂在墙上“大爱清尘”的海报,和那行悲壮的誓词,“能帮一点是一点,能救一个是一个”。在这行字下有座沙发,据说王克勤曾躺在上面做过一个属于他的中国梦:尘肺病在中国消失了。
与酒桌上的他一样,王克勤在生活中也是个坦诚、直接、憨厚的人。用他的话说,“我就是甘肃土话中的一根筋”。但这“一根筋”始终牵动着底层民众的痛苦与悲情。王克勤出生在甘肃农村,在那个贫穷动荡的年代,自然灾害中他忍受过饥饿,三次生食土豆中毒都幸运地被赤脚医生捡回性命。儿时随大人搭火车去兰州换粮食,因被列车员嫌弃,目睹了亲人被甩耳光的场景,在旁人的碎语中被勒令打扫车上的卫生。进城后看见城里人餐桌上吃剩的三个包子,战战兢兢地取走,与同乡的几个孩子分着吃,至今难忘那份香甜。王克勤珍贵之处,不在于对底层民众居高临下的怜悯,而在于那份感同身受,将心比心。在他看来,作为一个普通农民,自己与亲人都有过同样的遭遇,都在困苦中坚强生活,怜悯自己的父母,是种罪过。
说到他的家人,不止一次看到各处对于王克勤执拗迂腐,负疚家人,不值尊重的种种质疑。当问到这一切,复杂沉郁的表情,伴着欲说无词的唇动,他终只能挤出一句,“是我对不起他们”。
这背后积蓄的庞乱,以及无处启齿的无奈与怨苦,只有这位知天命之年的西北汉子才能消化。
如果你认为他有负家人,求仁舍义,那么请理解一个性情中人,在决断理想与家庭间的万般自责与酸楚,与一位妻子二十年的担当与坚定。如果你难懂这份于私无关的帮呼,那么请理解一个将心比心之人,面对众多生死一线境遇时,情难自禁的无奈。因为去理解,去感受,去倾听,正是普罗大众深藏的美德。
在这个喘息的时代,王克勤是为数不多愿意静待下来,倾听痛苦喘息声的人,也正因为他的存在,才让我们猛然回觉,同一时空中,由于承载过重的发展代价,许多人早已落后了很远很远,而他就是那跟牵扯在主流生活与遗忘深渊的纽带,为了不让割裂无法挽回,为了不让良心迷失在追赶的路上,他始终维系着这种可能,却不断被两端撕扯,越绷越紧,痛苦感越来越强。
即使这样,他依旧相信希望,因为民间在回暖,遗忘在被对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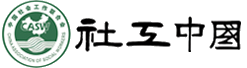













已有0人发表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