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注:采访成于2018年11月,原为纪念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暨北京大学社会工作专业重建30年。阮曾媛琪教授及同时代的那一批社会工作前行者,他们把家国之思融入了“与祖国同行”的脚步中,使得社会工作爱国、爱党、爱人民,有原则、有温度,也有力量。
阮曾媛琪,时任香港理工大学校长高级顾问及应用社会科学系名誉教授,曾任香港理工大学副校长。香港大学社会科学(社会工作)荣誉学士、多伦多大学社会工作荣誉硕士、英国曼切斯特大学教育硕士、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行政哲学博士。
阮曾媛琪教授为香港高等教育资助委员会委员、凯瑟克基金会理事、百䝨亚洲研究院执委、香港公共行政学院理事、香港社会工作人员协会名誉会长、全国妇联执委、中国社会工作人员协会荣誉顾问、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顾问、中华女子学院发展理事会理事、北京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海外人才工作顾问、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第六届理事会理事、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联席主任、国际社会工作教育联盟前主席。
阮曾媛琪教授曾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委任太平绅士及铜紫荆星章。2017年度中国十大社工人物。2018年获陕西省授予“一带一路”教育合作贡献奖。
(以下访谈,“问”指同学提出的问题,“答”是阮曾媛琪教授的回答)
赤子丹心
问:您是如何与社会工作结缘的,为什么会想到来中国大陆开展社会工作教育和服务?
答:我中学的时候就很幸运,当时我有好几位年长老师是燕京大学及西南联大毕业的,她们上课的时候很喜欢与我们分享她们年轻时的故事,并熏陶我们要以国家及人民福祉为重。大概是受我中学老师的影响,我心里一直很想服务祖国。
初中三年级时,另一位从英国来的音乐老师带我们到当时的三不管地带——九龙城寨去服务一些最贫穷及犯罪人群,并看到很多以前的罪犯得到洗心革面,故此我一直希望能以社会工作去帮助人。
当我在香港大学选读了社会工作专业之后,我就更深信社会工作这个专业是一个能够服务人、帮助人、并能带来社会正面改变的专业。
后来我又先后去了加拿大及英国深造社会工作及教育,之后我和我爱人去新加坡工作,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教社会工作,当时的工作条件十分好,但是当时心里一直就是觉得对不起我的祖国,对不起我的理想,因为我一直都是想要服务祖国的。
但去了新加坡亦给我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令我有机会我被选为亚太区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的义务秘书。上任之后,我就和主席说:我有一个心愿,我就是想服务祖国,希望能够有机会参与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
当年有一首《中国梦》的歌对我的影响很大,我一直都很希望能够服务祖国,让老百姓人人都能够过幸福快乐的生活,而我深信社会工作是可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的。所以当时我就建议协会成立了一个“中国联络小组”,由周永新教授做主席,傅德彤先生作司库,我做秘书。
但是其实当时成立了小组却不知道可以做什么,毫无头绪。到了1986年,我回到香港理工学院工作,有一天周永新教授给了我一个名片,这张名片上的人名叫顾宝昌,是当时北大社会学系的副系主任,原来北京大学即将开设社会工作专业,我当时就很兴奋,写了一封信给顾宝昌,信中说希望亚太区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和北京大学可以合作开展一个研讨会,探讨中国社会工作,他立刻就回信说可以,我开心得不得了。
后来王思斌老师告诉我,原来当时刚开完马甸会议,民政部和教育委员会都大力支持北大重建社会工作专业,并投放了一百万元支持北大的社工专业,故此大家都对北大充满期望。所以当时有这样一个契机,把我们聚到一起。

后来袁方教授和王思斌教授一起来香港考察及取经,袁教授真的是一位非常有心的老师,因为他和费孝通教授及雷洁琼教授那一辈是看过1952年之前的社会工作,虽然那时候的社会工作很偏西方,但是知道社会工作是好东西,能帮助解决一些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问题。
袁教授就常常告诉我:阮太,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好,一定要把社会工作课程办好。后来我们在1988年底就很成功的举办了此次会议,来了100多个人,反响很好,也取得了很好的阶段性成果。
筚路蓝缕
问:所以就是这样一个契机使香港理工大学和北京大学建立了联系吗?
答:是的,就是这样香港理工大学(1994年之前称为理工学院)和北京大学开始了30年的不解之缘。我记得那时候北京大学已经收了第一批社会工作本科及硕士学生。
大概是在1990年左右,袁方教授和潘乃谷教授与理大社会工作系主任麦萍施教授商量可否派老师来北大教《社会工作导论》这个课程,因北大当时未有受过正规社会工作专业的老师。
当时我们在理大系里也有一个辩论,我鼓起勇气表示我想去教,因为我觉得社会工作是对老百姓好的,所以我们应该去帮忙。
我的系主任和副系主任都支持我的想法,而且我在香港和新加坡也是教《社会工作导论》,所以我就和我另一个同事宋陈宝莲来到了北京大学教书。当时觉得应该不难,想着就是把我们在香港及新加坡的教材拿过来教,把英文翻译为中文便可。
但是开始教之后,我们发现在中国内地推行社会工作和在香港和新加坡及海外是完全不同的。当时王思斌老师就坐在教室后排,而北大的学生及老师总是提问一些似是简单但其实十分深奥的问题,比如问“社会工作本质是什么?”因为有很多的文化、价值观都是不同的。
他们当时问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都是关于价值观的,比方关于“自决”、“私隐”及相信每个人都可以改变等这些在社会工作专业中一直都觉得是很自然的概念,我们觉得在香港几十年就是这样教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们却觉得不适合内地。
比如他们就不解在中国若未婚妇女怀孕了,难道不应该让家里人知道及共同讨论对策吗?比如有一些罪行很大的人也可以改变更新吗?经过这个课之后,我们有了很多讨论,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深层反思,觉得在中国推动社会工作必须先了解国情,不可把西方行之已久的社会工作理念及方法照搬应用在中国。
我很清楚地记得在我们总结会议的时候就有一个激烈辩论,当时理大的麦萍施主任就提出如果要把社会工作在内地推动、发展的话,一定要经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一定要考虑中国的国情。
她认为理大老师不应再教了,不是我们不帮忙,而是我们不能教,没有资格教。如果为了中国社会工作长远发展的话,我们应该陪伴北大及国内社会工作老师一同走这段路,而不是把我们懂的东西照搬过来。
故此我们决定要选择一条较难走的路,就是要以伙伴的角色陪着内地社会工作老师一起走这段路, 要增强内地社会工作老师们的自己的能力,去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工作专业。
问:作为同行者的这条路是如何开始的呢?
答:当时我们共同讨论出一个方案,就是北大及理大的老师每年一起到海外学习,尝试了解国际社会工作专业的惯例及模式,然后一同讨论及反思,并尝试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工作道路。
很幸运,我们当年得到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教授史蒂文森教授的大力支持,并获得英国文化协会的基金资助,他们与我们签订了五年合约进行香港理工大学-北京大学-诺丁汉大学三方合作的项目。
每年我们都和北大的老师一同去英国去考察,并且我们每次去都邀请了相关部门的人员,所以我们也邀请了教育部、民政部、妇联的同事一起去。
因为我们觉得需要把他们连接起来建立网络,这样可以为他们提供合作机会。我们每年的团队在10个人左右,大家关系特别好,同甘共苦,我们在过程中一同学习,一同反思,然后回到国内再分享给其他人,每年有不一样的题目。
第一次学的是社区照顾,然后又学实习、社会工作课程设计、跨文化社会工作实践等,诺丁汉大学为我们安排了多元化的学习方式。我们每次回来都会在北京开一个公开的研讨会,有来自香港的老师、英国的老师、内地的老师,一起进行探讨和总结,再把我们所学习到及总结出来的专业知识传出去。
我们也出了几本书的,比如,《社区照顾》、《社会工作的本质》等。对于北京大学的老师们来说,他们在反思的过程中,就慢慢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路,这些深层次反思是极重要也是极艰难的过程,但亦是十分有挑战及有意义的,这个是我们的开始。
此外,亚太社会工作教育协会方面,我们针对大陆的社会工作老师,动员了许多香港、台湾及海外华人社会工作老师及资深工作者, 在90年代初期安排了一连串的短期的培训、考察等。
到了1994年,大陆成立了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当时是在与亚太区社会工作协会合办的研讨会中宣布的,大家都十分兴奋。另外,当年麦主任就提出,如果要跟中国内地的朋友一同走这条路,他们一定要有自己的书。
所以当时我们就从德国米苏尔基金会申请了四百万元资助。成立了四个图书馆,分别是北大(代表高教系统)、民政干部管理学院(代表民政系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代表青年系统)、中华女子学院(代表妇联系统)。
我们希望在各系统牵头的地方成立一个图书馆,这个图书馆不单服务自己相关的系统,也可以互相借书。
我们的目标就是让大家有机会阅读学习最经典的书籍,但是各个图书馆又有不同的侧重点,比如北大在社会政策方面的书比较多、中青院图书馆在青年这部分的书多一些等,各个图书管理员都来香港学习如何管理图书。
我们这方面的目标是给大陆的老师增能,帮助他们掌握国际社会工作知识及资讯、发展本土的社会工作。
到了1999年,当时各大学的社会工作专业开始扩招。我记得那时候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举办第二次会议,1999年在中青院开的。
我们之前去社会工作任何的研讨会都是很小的,但是那次一进中青院的会议厅吓了我一跳,有好几百人。
那次可能已经有40个以上的院校开展了社会工作学科,但是开会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参加会议的人很多都不懂社会工作,大家都是来自其他学科的,并且都过来问我们要课本,问我们怎么教这个专业。
所以我们就很担心,我记得我问王思斌老师说:“我们怎么办?”。一方面高兴,我们就觉得快当然是好事,因为那么多人有兴趣发展社会工作;但另一方面我们担心的是,这些对社会工作完全没有认识、没有经验的人怎么去教学?
我们之后就商量做一个真正的、长期的、深度的社会工作硕士课程,而且我们希望让那些老师真正经过专业的培训,包括正规的实习训练,而且要做不少于800个小时的实习。
历史责任
问:在这个过程中有怎样的困难,我们是如何克服的呢?
答:那个时候困难很大,从1991年开始的十年,我们一直都在香港办一些短期的、一星期或者两星期的培训。但是后来就觉得是不够的,一定要搞一个正规的MSW,所以就开始探讨这个可能性。
当时我们遇到很多困难,因为要做这样一个硕士的课程,一方面在各个单位需要审核通过,经过很多关卡,另外还要找资金资助, 还需要找老师,而且授课老师都必须是最好的老师不仅要理论基础好,还要实践经验很丰富。
那么我们就开始筹办这个课程,但过程十分艰辛。我还记得有一天我打电话给王思斌老师,我说:“王老师实在太困难了,又没钱又没人,真的很难, 实在不行的话就算了,我们就继续做短期培训。”王思斌老师停了一阵没说话,之后说:“阮太,这个是我们的历史责任,我们不可以不做。”所以他讲完这话后我又重新振作去张罗了。
其实王老师牺牲很大的,因为他当时是社会学的,而且大家都觉得他就是“明日之星”,其实当时已经是“当日之星”了,他是领导,年轻有为,而且学术又好,所以当时有的社会学界的老师不理解,说你王思斌干嘛要搞这样一个操作性的专业?
王老师常常告诉我,他有很大的压力,但是我觉得我很敬佩他,因为他愿意,他是选择了社会工作,他说他是农民出身,所以他觉得社会工作应该能够帮助老百姓,尤其是农民。
而且他坚持北京大学社会学和社会工作是一同的,不要分开,因为社会工作与社会学是互相紧扣、互相支持的。
当时就因为有这个理想,就是一个梦。就这样,我们在香港理工和北京大学两边都通过审核了,后来凯瑟克基金会就支持了我们这个课程的开支,当时需要至少三百万,但得到他们的慷慨支持。
当时只打算办一届,但后来因社会工作教育不断扩展,故一共办了七届,而凯瑟克基金会亦支持了七届,历年共投入了数千万元。
我们的学生都已经是教授或者讲师,来的都是很厉害的人,我们教师也有很大压力,但是我们都很愿意教,很开心,他们都是有理想的,都是认为社会工作对我们国家和老百姓有用的人。
第一届是15人,第二届20人,第三届40人,一共七届,共235个学生。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互相学习,每一位学生都是我们的同伴,他们都很厉害,这些学生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在整个过程里面不断的去反思,来这次会议之前我专门拿出了第一届招生简章看,我很开心地看到当初定的四个目标都实现了。
第一个目标是“培养一群可以领导社会工作及社会工作教育的老师”。第二个目标是“理论与实践整合,既要有高度,又要扎根老百姓”;第三个是“发展本土理论和实践”;第四个目标是“帮助这些学生建立一个互相支持、互相学习的网络,继续推动社会工作发展”。
问:您是如何在中国大陆进一步拓展社会工作教育和服务项目?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些在教学过程中所做的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工作教育和服务项目吗?
答:我们这个课程通常是用他们的假期学习,我们是要求他们有800个小时的专业实习,并且我们的实习也很严格,所以他们非常辛苦。
提到这个我想到一个令我很开心的地方,就是我们在授课的过程中,发展建立了很多社会工作实习基地(项目)。
我们当时在内地有找既有的实习基地(项目),但是还是觉得应该建立实习项目让这些学生去实习。2000年开始的这个课程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找实习。
并且我们觉得,如果在大陆做MSW不做农村社会工作的话是对不起祖国的,虽然我们香港的老师对农村一无所知,但是我们坚持做农村社会工作。
当时我们招的学生都是老师,有一位来自云南大学的张和清老师(现在是中山大学的教授),我当时就跟他说我们要把你培养成为未来做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人,你有没有兴趣?张和清老师就一口答应了我们。
我们当时就在云南找一个地方,就是要找一定要有政府的、得到居民的同意的、可以持续发展的地方,张和清到处去找,找了几个地方,向荣老师也陪我们去找,最后定了平寨,在那里开始了农村社会工作。

当时很幸运,古学斌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帮助我们一起做社会工作,我们用口述史的方法去了解农民的声音。我们还用社会工作方法去做社区发展,在北京西城区用社会网络模式去帮助妇女。
第三个项目在上海开启社区矫正的工作,主要是解决边缘青年的问题,尝试用家庭-劳教学校-社区进行互动,用参与式的方法去增能。
第四个项目我们还在湖南发展了一个残疾人社区照顾基地,用社区照顾的方法,尤其团结年轻人去帮助家访、照顾那些残疾人,协助残疾人与社区共融。
第五个项目是在昆明的第一医院做精神健康社会工作,当时的精神病人都是用药物治疗或甚至关起来的,我们就尝试用社区照顾的方法,让那些痊愈的患者回家,引导社区的人帮助患者自我恢复。
第六个是我们在哈尔滨开展了企业社会工作,当时应该是国企改革年代,我们就意识到如果解决不好这个矛盾的话,对于我们整个国家的平稳发展是有威胁的,所以企业社会工作的理念就是希望可以在企业转型的过程中能够运用社会工作方法预防问题的产生,有问题我们提前解决,比如关于“裁员”,我们就预先帮助他们找工作,在心理上进行辅导,同时企业也积极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模式也很成功。
第七个是我们在汶川地震的时候开展灾害社会工作,在灾后重建、能力建设方面进行探索,协助灾区居民藉自助及互助去进行重建,比如“映秀妈妈”就是好例子。
最后一个是民族社会工作,我们在新疆及陕西有好几位毕业生,都是高校老师,我们鼓励他们应用社会工作方法去尝试促进共融,他们让汉族和维吾尔族的孩子一同活动,创建“儿童中心”、“家庭中心”,孩子们来,家长们也会来,一同建立互信的关系。
后来民族大学的任国英老师来开年会,我就跟任老师说要不要来读MSW,任老师当时已经是大教授及院长了,但是任老师真的来读了,我们很感动。
一般我们的学生在做了这个项目之后都变成了这个领域的专家,我们也希望这些学生可以做接班人,慢慢进行本土化,探索更多的新内容。
诲尔谆谆
问:社会工作发展至今步步艰难也硕果累累,您对中国社会工作的未来有什么怎样的期待呢?
答:其实目前很多问题都可以进行尝试的,社会工作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并且有一种转化的力量,它可以转化我们自己、转化学生,转化服务对象,甚至转化社会。
我深信我们可以通过社会工作的转化力量带给人们希望和幸福,促进社会的进步及和谐共融。我们必须要有这个信念,若只看到困难便会裹足不前,但若有理想和决心才能一步一步地朝着目标向前迈进。
我们的社会工作之所以可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是因为我们不是独行者,我们有很多伙伴一同去做,我们的学生、服务对象、政府部门、基金会都会是合作伙伴,都是战友。
我们这三十年来共同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工作模式,是独特、具创新性及颇有成效的,我们很希望可以把我们中国的经验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启发他们去建构适合他们国情的社会工作模式。
故此我们在今次庆祝三十年社工在中国内地重建研讨会,亦邀请了12位“一带一路”国家的社会工作教育领袖,与他们分享中国的经验及发展道路,亦让他们看到我们这样一种合作伙伴关系是可行的。
我们相信社会工作是一个跨文化的专业,亦是一个可以推动国际和谐共融的语言,故此我们希望社会工作能够成为桥梁,促进国际对话及和平合作。
我认为社会工作的未来是光明的,在下一个十年,我希望我们中国可以把我们的既具国际水平但同时具本土化特色的社会工作理论及模式走出来。
同时,希望我们可以积极建构未来的社会工作理论及实践模式,并在国际社会工作群体中发声, 把中国的经验与国际社会分享,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社会工作群体所建构的社会工作学派能够与欧美各国的社会工作学派分庭抗礼,并成为社会工作的主流部分,影响国际社会工作的发展,贡献人类福祉。
未来在你们手中,现在你们要接过接力棒,坚持自己的理想,为社会工作专业去为国家及人民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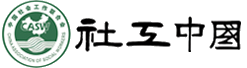













已有0人发表了评论